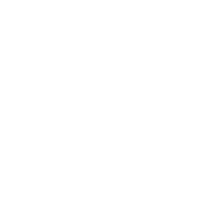12月23日,中牟县人民法院的法庭外寒风凛冽。梁先生攥着妻儿的照片。这一天本应是妻子30周岁的生日,按照河南老家的习俗,该是全家围坐一桌,孩子们吵着要分蛋糕的喜庆日子。如今,他的岳母只能把蛋糕、水果、孩子们爱吃的蛋挞和薯片,默默摆放在三座新坟前。
“他们娘仨一具完整的身体都没有,面目全非。”梁先生的声音里没有哭腔,只有一种被掏空后的麻木。尸检报告上的文字冰冷如刀:妻子头部、颈部、躯干多处锐器伤,外加软质带状物勒颈;8岁儿子左侧肾动脉破裂、横结肠破裂;7岁女儿被软质带状物勒颈窒息。每一个医学名词背后,都是一幅人间地狱图景。而制造这场地狱的,竟是梁先生口中“二十多年白玩了”的发小崔某某。
“农夫与蛇”现代版
这起案件最令人脊背发凉的,不是抢劫杀人本身,而是凶手与受害者之间那层层叠叠的“人情网”。两人从小一起长大。梁先生在北京学美发时,带着崔某某北漂五年;后来崔某某去新疆发展,后又回中牟在梁先生父亲的船厂待了三年。最讽刺的是,案发前,崔某某和父亲就睡在梁先生的废品站点,晚上还常回梁先生家吃饭。梁先生的妻子,那个后来死在崔某某刀下的女人,曾为他做饭。崔某某甚至说过“特别喜欢”梁先生的孩子,还说要和他女儿结娃娃亲。
“我要是知道的话还会和他玩吗?”梁先生的质问,其实是所有受害者的共同困惑。邻居后来才告诉他,崔某某小学后就“偷完这家偷那家”。二十多年的交往中,梁先生从未听闻他干什么坏事。“这个人你根本想象不到他的恶”,这句话里透着深深的无力感,我们赖以判断他人的经验系统,在此案面前彻底失效。
熟人社会的信任,本是中国乡土文化最珍贵的黏合剂。谁家有事,邻里帮忙;发小之间,更是“光屁股长大的交情”。可崔某某用偷偷配好的钥匙,在凌晨潜入恩人家中时,所有这些情感积累、道德约束、人情脸面,瞬间化为乌有。他用来寻找黄金的手,曾是接过女主人饭碗、也抚摸过孩子头顶的手;而这双手,终成了夺取他们性命的凶器。
罪的掠食性
刑警给梁先生的解释只有四个字:“农夫与蛇,恩将仇报”。这八字背后,藏着一个更深刻的命题:罪如何从潜伏的种子,长成吞噬三条人命的怪物?
圣经《创世记》中上帝对该隐的警告,在此案中得到骇人的应验:“罪就伏在门前;它必恋慕你,你却要制伏它。”罪的最初形态,往往伪装成普通情绪,一点嫉妒、一些不满、些许贪念。崔某某的恶,并非一夜成形。从小学时的“偷完这家偷那家”,到成年后需要依靠发小接济,那些被轻易原谅的“小恶”,如同潜伏的掠食者,在暗处悄然壮大。
我们社会常有一种天真的假设:人本质是好的,极端恶行只是特例。但无论是纳粹屠夫艾希曼的“平庸之恶”,还是此案中崔某某从“蹭饭的发小”到“灭门凶手”的蜕变,都在警告我们:罪具有成瘾性和扩张性。第一次小偷小摸时的忐忑,到后来入室抢劫的狠戾;第一次挥拳时的犹豫,到后来刀刺孩童的残忍,这不是“突变”,而是“渐变”。
崔某某在法庭上或许会被鉴定为心理正常。这才是最可怕之处:一个心理正常的人,如何能对叫着“叔叔”的孩子下手?答案可能在于,当人长期将他人工具化——无论是将发小视为可索取资源的对象,还是将妇女儿童视为达成目的的障碍——他的人性感知便会逐渐麻木。罪就像癌细胞,最初只是几个异常细胞,若不切除,终将吞噬整个机体。
法律判决与灵魂救赎的双重维度
梁先生的诉求很直接:“死刑立即执行。”这是法律维度最朴素的正义期待。但即使崔某某伏法,三个鲜活生命也无法复生,梁先生余生仍将活在“一具完整身体都没有”的梦魇中。
圣经中该隐杀亚伯后,上帝说:“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在中牟县的坟地里,同样有三种血的声音在哀告:妻子的血、儿子的血、女儿的血。他们向法律哀告正义,向神哀告不公,也向每个旁观者哀告,请不要再轻视那些潜伏在日常生活中的“小恶”。
此案暴露了我们在罪性教育上的双重缺失:一方面,世俗社会倾向于淡化“罪”的概念,用“心理问题”“社会因素”等术语消解个人责任;另一方面,传统熟人社会又过分依赖“人情”“脸面”等非正式约束,缺乏对人性幽暗的清醒认知。
罗斯福总统在二战初期无法理解纳粹的暴行,“人里面到底有什么,使得这些德国人能够如此邪恶?”直到阅读克尔凯郭尔关于“原罪”的著作后才恍然大悟。今天,当我们面对崔某某这样的案件时,同样需要一场关于“罪之本质”的公共讨论。这不是要回到宗教审判,而是承认一个事实:若没有对人性潜藏之恶的清醒认知,任何信任体系都是沙滩上的城堡。我们需要重建的,不仅是法律的外在约束,还有对“罪会吞噬灵魂”的内在警惕。
在这起案件中,正义最终会给出法律层面的回应。但对社会而言,问题不止于判决。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人类最危险的盲点,不是恶的存在,而是对恶的低估。信仰之所以不断谈论“罪”,不是为了制造恐惧,而是为了制造清醒。因为只有承认那头掠食者真实存在,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需要约束、悔改、彼此提醒。如果人心天然可靠,那么法律、道德、制度、信仰,统统都是多余的。
但现实一次次证明,恰恰相反。这也是为什么《创世记》中,上帝在悲剧发生之前,就已经发出警告;在悲剧发生之后,仍然追问该隐:“你兄弟在哪里?”那不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是在给人最后一次面对真相的机会。今天,当我们面对这样一起惨案,如果只是停留在愤怒、围观和转发中,而不愿意反思人性中那股被低估的力量,那么类似的悲剧还会以不同形式出现。罪如掠食者,可怕之处不在于它强,而在于我们总以为自己能控制它。而真正的智慧,是承认:它比我们想象的更狡猾、更耐心,也更致命。只有在清醒中,人才可能活得更谨慎;只有在警醒中,社会才可能少一些无法挽回的痛。
在这片土地上,有太多鲜血已经发出呼喊。我们至少该学会,不再对那伏在门前的东西掉以轻心。坟前的蛋挞会变质,薯片会受潮,但血的哀告不会停止。它问每一个活着的人:当罪伏在你门前时,你是否准备好了制伏它的勇气?
不再独自站在门前与罪对峙
信仰并不止步于警告。若故事只停在“你要制伏它”,那终究还是把重担完全压在人身上,而历史早已证明,人一次次失败。圣经对罪的理解之所以真实,是因为它同样真实地承认:人靠自己,最终无法彻底胜过它。也正因如此,信仰才会谈论“救赎”。救赎是为人预备一条不再被恶吞噬的路。
基督信仰所宣告的解决之道,是神进入人的处境。那位看见亚伯之血呼喊的上帝,并没有只停留在追问和审判中,而是在后来亲自承担了罪所带来的代价。十字架是对罪最严厉的定罪,因为它必须以生命来偿还;它也是对人最深的怜悯,因为这代价是由神自己承担。
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可以退场、责任可以模糊、正义可以打折。相反,正因为相信罪的真实和代价的沉重,才更坚持公义必须被执行。但法律能约束行为,却无法医治人心;制度能延缓灾难,却无法根除根源。若人心仍旧空着,那头掠食者只是在等待下一次机会。
真正的盼望在于:人不再独自站在门前与罪对峙。当人承认自己的无力,转向那位比罪更大的救赎时,生命才有可能被重新塑造。不是靠一时的愤怒、道德的自律,或舆论的声讨,而是靠一颗被更新的心。那才是罪真正被制伏的开始。
鲜血已经发声,历史也早已作证。若我们只学会更愤怒,却不愿更谦卑;只想控制罪,却不愿被拯救,那么悲剧只会换一种面孔重来。但若人愿意承认:自己并非站在审判席上,而同样站在危险之中,那么救赎,就不再是遥远的宗教词汇,而是这个破碎世界最迫切的答案。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安徽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