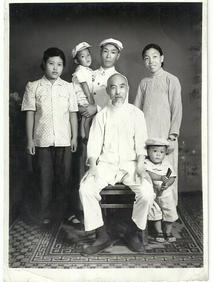两条煎得金黄的小鱼在锅里灵巧地翻了个个,李姐掂起铁锅,将鱼滑进一早放在灶台上的淡青色盘子里。打开一旁的水管,将锅冲洗干净,擦拭到锃亮,开火烧干,放油,待油滚烫,一把浇在铺满葱姜蒜的鱼肉上——滋啦——今晚的主菜成了。
香味弥漫,南方潮湿的港口渔村,厨房没门,为方便通风,敞开处的另一头正对灶台后的窗户,鱼肉的鲜味儿和佐料的辛辣毫无阻隔地飘来,霸占整个空间。
李姐无暇自得,有两位年轻姊妹远道而来。她打开冰箱,绿的、黄的、红的、白色的食材松松散散塞满三个格子,心里一暖,念起送菜的老信徒。不消多想,用辣酱赶快拌出一道凉菜来。五月雨后的南城下午,少不了黄瓜的清凉可口。
还有她从抖音上学来的苦瓜蒸鸡蛋。切掉苦瓜两端,蛋液淋在里面,锅里蒸熟调味。李姐还记得,女儿喜欢看她搞这些创意。
风从港口吹上来,吹起她黏在脖子上的头发,她专注在案板、灶台、冰箱、置物架之间。切菜声、蒸煮炒菜声传到大厅。这座渔村教会已久无人造访。
渔村在海边,也在山上。边陲沿海,从700米的隧道穿出,车进入山群。山很密,比一般的山更厚,离得近,不是站着,似是坐在车边。国道挑拣着适合的山体延伸,鲜少直线。车在两山之间的夹角穿梭,往群山腹地开去。
越走越深,从西峰绕到东峰,忽见大海。朝着大海,开到地势最低处,路变得坑洼颠簸,旁边的土方露出被铲敲的痕迹,再路过两座在建的祠堂和寺庙,伴着鱼腥味,车停在一片滩涂前。这就是渔村社区在打车软件上的定位点。
“你们往上看,看见十字架,顺着楼梯能上来。”老叶带着南城口音,他是李姐的丈夫,平时在车程二十分钟外的另一个乡村教会服侍,一个多月前左脚骨折,到妻子这里静养。
滩涂旁是三四十米高的山丘,教堂和人家贴山而建。老叶每月来这里一次,丘上分布两千多灶头,除了几横几纵青石板路,走得多了,老叶发现,各家各户总能从房前房后攀出新的小路来。王大姐平常也在教堂礼拜,她领人走最方便的一条,除山脚处一小段石梯,往上大多是斜坡,左三拐右四拐,进一个四合院,照常跟院里邻居打声招呼,从偏门出来,再拐进一条小路,教堂就到了。
从任何角度,都无法拍到这间教堂的全貌。山似乎是青石头垒成的,房子一间挨着一间,前后高低错落,间隔只两人宽。并排两户,一跨步就是另一家。贴着门根往上看,两层的教堂向天上伸出高大的错觉。门上留着圣诞节的红色条幅,褪色的小三角彩旗黏在铁门上方的栅栏上。
门左侧,介绍宗教场所管理人的告示还新,没有斑点,负责人、财务、执事清晰可见。像这样的管理举措,近半年来越来越多。张贴负责人是最简单的一个。
教堂前侧的水泥墙上,李姐摆上几盆多肉,刚下过雨,多肉喝得饱饱的。老叶拄着拐杖,倚在这个墙头,跟客人打招呼。
“这里基本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像我们这样的都算年轻。”老叶穿着蓝色T恤,将受伤的左脚抬起来放在右腿膝盖上。他今年五十多岁,国字脸,有南方人的饱满额头,厚嘴唇。皮肤粗糙,但眼睛很亮。
光滑的皮肤和明亮的眼睛在渔村已经不常见。男人打鱼,女人织网,就像四季一样不会改变。开渔出海几月,禁渔期在内海简单拾捡,加上女人操持,一年下来,每月能收获几千。某年,国道修到渔村,又有政策彻底禁止禁渔期捕捞,城里打工一个月随便能五六千,人们再没留在这儿的理由。老叶和李姐住隔壁县乡下,2000年左右,他们也离家,到湖州打工。“实在走不掉的人才留下来。”
教堂隔壁有一扇半开的门,黑白电视放着老故事,头发灰白的老人佝偻在椅子里。山脚下三四个唠嗑的奶奶。坐轮椅的王婆,守着海鲜杂货铺的李婶。她们是被留下来的人。
作为织网女,她们很少人有机会读书。老叶发现,同样都没赶上义务教育,但湖州的老太太有文化。那里的人觉得,“男孩子不读书不要紧,女孩子一定要读,不然嫁到别人家要吃亏。”但渔村人说,“女孩子反正要嫁出去,读了也没用。”不如织网勤快点,一个月挣下五六十,“谁还送你去读书。”
2024年,李姐被渔村教会聘用,她发现,这些老奶奶将是自己主要的服侍对象。
“你家媳妇是外地人吧,”刚回来常有人跟丈夫开玩笑。十里不同音,加上在外打工多年,她要先学会渔村话。偶有年轻人误入,问路也问不明白,村里人听不懂普通话。礼拜当然也如此。
儿子小叶在湖州出生,只说北方话。在距离渔村七十公里外的一家大教堂服侍,李姐对他的嘱咐是,把意见放下,先学好本地话。
六十年前,山岙外开始推广普通话,风潮到了渔村,被渔船重又带去海上,村内鲜有痕迹。跟语言一样固守渔村的还有敬拜方式。一楼大厅,三张暗红木圆桌,另有一张不锈钢浅碗摞起来,堆成三角形。主日中午爱宴是南城教会传统,但李姐还记得,四月开展小组,她预备水果、零食,将桌子擦得干净,老信徒不愿意,“聚会不能吃吃喝喝。”
南城一家二三千人的教会,几年前重新建堂,在LED屏幕的放置点上发生分歧。经信徒代表大会和长执会慎重讨论,最终只悬挂LED屏在主堂前方左右两侧墙壁上,正中间依然悬挂十字架,且必须是暗色木料材质。“进入主堂,正前方必须是十字架。”该堂负责人解释。此外,哪怕人数之众也不分堂,因主日全天献给上帝是本地传统,分堂也拦不住信徒一天都来。
传统里有敬虔,李姐明白,她很快将水果零食换成茶水。分组坐在一起,喝茶谈道,老长辈们接受。但轻易不“谈”,从去年六七月到现在,主要靠李姐讲。跟儿子带组不同,李姐的小组从识字读经开始。
咿咿呀呀时,她感谢这些弟兄姊妹,渔村教堂是他们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开渔期、圣诞节和春节,城里青壮年回来,也带回奉献,但像李姐这样全职工人的工资,还主要依靠“老本”。它们和现在的鱼肉、黄瓜、苦瓜和土豆一样,都来自老一辈弟兄姊妹的爱心。
但他们会渐渐离开,“追思礼拜已经成了乡村传道人的一大工作,”22年老叶的教会一年送走64位信徒,23年46人过世,24年41人,截止今年5月,教会又已送走11位长辈。
女儿叶玲也在同一家教会服侍。2023年,一家四口终于得着时间要去北京旅游,当初小叶北京求学,父母一直没机会前去,这次要弥补遗憾。真要成行时,叶玲却被拦住了。
一位老信徒即将过世,医生说就三五天内的事儿。叶玲得为他做临终祷告。五天过去,爷爷还清醒。一星期过去,叶玲想要不先去北京,回来应该还来得及。但又不放心,害怕真出事。等着等着,老爷爷硬是又撑了一个月。
老人离开一段时间后,那年夏天,叶玲却因病过世。那是全家最后一次能一起去北京的机会。
“服侍里就是这些细碎。”提起这件憾事,说不明白,李姐觉得心酸,也滑稽,甚至笑了起来。
“姐,弟弟想你了。”叶玲过世一周年,小叶在朋友圈里说起过去她的勉励,“当每一次的经历都能让我想到‘主耶稣要我学到什么’,就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了。”
当被问到如何看待当下传道人工资待遇有所不足的情况。小叶的回答还是来自叶玲,“既然全职服侍,就不要想着工资,这样拿到的时候都是恩典。”
同在一桌的教会领袖加了句,“侍奉的人不要斤斤计较,教会考虑要面面俱到。”
有人给小叶介绍对象,李姐没什么别的想法,只是希望女方不要太娇气。传道人的妻子,注定会比较辛苦。
李姐和老叶也是经人介绍认识。二十几年前,两人读圣经班,同学都是教会的青年义工。现在南城除了市中心两个教堂,其他教会已很难看见四十岁往下的年轻人。圣经班还在办,但报名的都是无处可去的小年轻。今年开学后没几天,圣经班被迫辞退两个人。
叶玲和小叶二十几岁进教会服侍。老叶言语里不乏骄傲,“我很感恩这两个孩子愿意走这个路。”
“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事奉耶和华。我是受这句话的感动。后来自己追求知道了,在这个世上,无论你是百万、千万、几个亿的资产,在这个世上不过肉体过得快活一点,走了都不被纪念。唯独做永恒的事工,以后会被纪念。所以,我全家就走这个路。”
几年前,渔村唯一一所幼儿园关门。村里更安静了。李姐发现,庙里的香火更旺了。
偶有客人来访,李姐会带客人在村里走走。最靠海的地方有一个“南天门”,一所天后宫。香炉不歇,香灰积的很厚。巧的话还能遇见谁家门前搭棚,这是在请道士做法事。进村处,新修了某家宗祠。高铁从小叶的城市驶向南城,田地、山岙里,不时掠过或复杂或简单的寺观。
最漂亮的,是渔港东头的观景台,两层,用彩虹色楼梯连在一起。站在这里往村里望,会看见被刷成蓝色的船样的社区活动中心,白色的有红色十字标识的卫生所。两个建筑物前的空地上,木头路标指向渔村各个“景点”。
好几年前,领导决定开发渔村旅游项目,投了不少钱。领导换了,项目停了。
李姐为了把信徒找回来,经常出外探访。她会路过刷了一半的蓝色房子、三分之二刷白的墙,和句子只剩半边的心形打卡点。想起老叶在的那个乡镇中心堂,因为负责人不同意,小组不了了之。
但渔村教会还在,李姐的脚步也没停。
巧合的是,夫妻俩的名字里,藏着两个字:悯与希。一个是怜悯,一个是希望。
雨停了,风静了,空气重新凝固。在被定格的渔村里,李姐踏上石板路,探访还在继续,六十人,八十人,一百人。
(本文人物和地点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