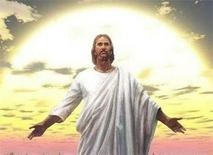大家知道,我的笔名叫“洪道”。“洪”也可指“大”或“程度高”的意思,那么“洪道”即隐喻“道具有宏大的影响力”。笔者期盼这真道能广泛影响我们的侍奉与生活,好让我们能在凡事上尊主为大,让祂得当得的荣耀。俗话说“文以载道”,文章只不过是载体罢了,其形式可以多样化,但其所承载的应当是真理的道。
在汉语语境中,“道”一般指“道理”“道德”“道路”。汉语语境体现出了汉文化注重“功能”的特性。但我们知道“道”的本体也很重要。人们必须先确定“道”是什么,才能进一步确认“道”有哪一些功用。在这方面,上个世纪的国人似乎已经有所察觉,他们先是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又干脆实行“全盘西化”。
在基督教方面,我们都知道上个世纪前半叶也出现了“基要派”与“自由派”之争,王德龙却认为这是另一种“体用之争”。他将“基要派”理解为“重体之教”,而将“自由派”理解为“重用之教”。
笔者认为“体”与“用”之间不应当是对立,而当是“道”的双重特质。因为严格来说,不存在“无体之用”,而“无用之体”的可能性也不大。人们习惯将某种文明视为“体”,另一种文明视为“用”,以拿来主义的思维理解“体用之辩”,但“道”既是宇宙性的;并不隶属于某个文明,这样的理解便是不合宜的了。笔者认为不管东方还是西方文明,都更倾向于“用”,因为“体”——真道的本体必须来自于启示,而非人的揣摩。
一、“道”与“道理”
“道”的希腊原文是logos,原为“言说、计算、尺度”,但赫拉克利特将其提升至哲学范畴,赋予其“宇宙理性法则”的内涵。赫拉克利特通过对日常事物的观察发现,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变化中,但这种变化却呈现出某种规律。于是,他认为宇宙中必定存在着logos,是宇宙中的“总理性”,这个总的理性支配着一切事物的运动。
赫拉克利特是希腊哲学家的一位代表人物,他对宇宙本原的追溯体现出希腊思维的理性特质,要从千变万化的现象中寻找出背后的“理”,然后再从各种理中追溯其最原始的那个理性,那个支配一切、隐藏在一切事物背后的“宇宙理性”。
不过,这种认识论并不能真正让人找到真理,这个世界宗教文化的多元性印证了这一点。人们从自己的经验演绎出某种理,继而形成某种宗教或某个知识体系,但这些宗教或知识体系往往是自我封闭的,一旦跳出自己的体系,就变得毫无意义。就好比瞎子摸象,瞎子摸到的确实是真实的,但他们将部分的事实当成了事实的全部,用人的逻辑推理在错误的前提中不断推演;然后自圆其说。
事实上,人靠自己有限的头脑是无法认识宇宙本原的,宇宙的本原只能通过神的自我启示才能被正确认识。理性的演绎一般来说具有三种途径:一种是透过“事实”来演绎,就像赫拉克利特所作的那样;另一种是透过“概念”来演绎,就像近现代唯心论的哲学大都属于这一类;最后是透过“神的自我启示”来演绎,这种演绎所得到的知识是最接近真实本身的。
二、“道”与“道德”
如果说“道理”是一种纯粹理性的话,“道德”无疑便是实践理性了;如果说“道理”所对应的学科是“科学”与“思辨哲学”,那么“道德”所对应的便是“伦理学”,教导人们应当如何分辨善恶及行事为人。在康德看来,上帝存在的合理性便在于人类的实践理性,因为“道德”存在的前提是“上帝的存在”“灵魂的不朽”与“意志的自由”。这是“道”在“道德”层面的功能性展现。
不过,康德是在否认了纯粹理性能够认识上帝的情况下才转向实践理性,故此他从实践理性中所了解到的上帝是一位“假设的上帝”。在这种情况下,“本体性的道”只是一种摆设罢了。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就有类似的现象,这种现象叫做“神道设教”。这是一种典型的“从下而上”的认识论。人们在道德实践的过程中感觉需要一位类似上帝的存在者来做人类经验的铺垫,因为没有这样的存在者,人类的经验便缺乏稳固的根基。
如果人们不承认先验性的存在,那么“道德”就成了自说自话的相对主义,甚至演变成为“道德的虚无主义”——那对人类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然而,由于人们只是需要“道”来建立他们的“道德”,对于“道”的关注也好,认识也罢,都是非常肤浅的。
大多数人对“道德”的理解只不过是“行为规范”,但随着传统文化的式微,后现代反权威主义的盛行,人们开始意识到“道德的危机”乃源于“信仰的缺失”。没有“道”的维系,所谓的“道德”只不过是一种外在的装束,难怪鲁迅会将宗法主义评判为“吃人的礼教”。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