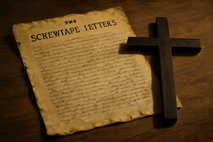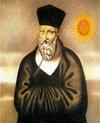重阳节那天,我陪着外婆去朝圣。夕阳余晖下,一个身形消瘦、面色憔悴的农妇,被一位中年男子背着前行。男子穿着粗布衣、黄球鞋,黑黄相间的牙齿显露出多年吸烟的痕迹。他们缓慢而艰难地挪着步伐,四周虽然有不少朝圣者,却静得出奇,只能听见男子细碎的脚步声——那不是铿锵有力的步伐,而是用生命最后一点力量在大地上探索这段特殊旅程的轻响。
他们并非夫妻,只是朝圣路上的萍水相逢。农妇身患绝症,无力攀登圣山;男子作为同路人,仅凭几个眼神、几句交谈,便决定背负她完成朝圣之旅。值得注意的是,男子比女子年长许多,在她面前展现出父亲般的怜悯与慈祥。正是这种"父女"般的关系,让这亲密的接触在路人眼中只剩下温暖与敬意,而没有任何暧昧的猜疑。
歇息时,女子递给男子一片干硬的面包。两人干裂的嘴唇费力地咀嚼着。夕阳的霞光洒在女子身上,她眺望前方,眼中突然绽放异样的光彩——圣山近在咫尺,或许只剩几十米,抑或十几米。此刻的夕阳,在她眼中化作了生命的曙光。
我默默递给他们两瓶水,点头致意。朝圣者之间自有默契:该说的长话短说,不该说的缄默不言;能用眼神交流的绝不出声,能保持距离的绝不凝视。这是外婆在我童年时就教导我的朝圣礼仪。
多年来,这些看似“迷信”的朝圣传统,于我就像科学真理般确凿不疑。我与这位女子,还有一段关于猴子的前缘。
十五年前,为安慰癌症晚期的母亲,我们全家登上云龙山。山顶有一对靠猴子招揽拍照生意的夫妻。我本希望“动物疗法”能给母亲带来慰藉,却目睹了令人心碎的真相。他们用饥饿训练猴子,将食物悬在远处诱使猴子完成高难度动作。这样既可以激发猴子的斗志;又可以抑制其惰性。这种“巴掌多于甜枣”的驯养方式。在他们眼中,猴子不过是受食欲驱使、永不背叛的工具。
这种驯养方式折射出人性最阴暗的一面,让我想起雷平阳的《杀狗的过程》——将狗的可怜与人性的丑恶展现得淋漓尽致。眼前这对夫妻与猴子之间,同样上演着这般血淋淋的奴役。母亲初见猴子时的惊喜,渐渐化作眼中无尽的悲悯,最终化作一声绵长的叹息。从她决绝的眼神里,我明白:这只猴子带给她的不是疗愈,而是更深的伤痛。
我们从夫妻口中得知动物贩卖链条的残酷真相,这促使我寻求动物保护协会的帮助,并撰文揭露。一方面想借此善行祈求母亲病愈,另一方面确实为这只猴子。母亲临终前的话令我铭记:“给猴子写文章,不如喂它香蕉。虽不能改变它的命运,但你的爱心能让它享受吃香蕉的两分钟。”正如外婆所说:“微小的善意虽不能改变世界,却能温暖眼前的生命。”
但我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即便解开锁链,这只被驯化的猴子仍会回到主人身边。它已忘记自由的滋味,正如夫妻曾得意宣称:“我们虐它千百遍,它依然摇尾乞怜。”这种根深蒂固的奴性,恰似人性的枷锁。
女人告诉我,她的丈夫已病入膏肓。这是因果报应吗?在罪与罚之间,他们选择放生猴子作为赎罪。但可悲的是,长期驯养已使猴子丧失野外生存能力,等待它的只有死亡。他们不知道,自己其实和猴子一样,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囚徒——他们解开了猴子的锁链,可自己的锁链又有谁来解开呢?
朝圣山上,女人最后的祈祷给出了答案:“祈愿上帝赐我丈夫病得痊愈,即使我自己受苦万分也心甘情愿。祈愿上帝饶恕伤害我的人,也祝福被我所伤害过的人。我为被我伤害过的人祈求祝福,我也饶恕曾经伤害过我的人。”
难道,这就是灵性之光带来的改变与奇迹吗?牺牲与舍己,体现在妻子对丈夫的这种患难之爱之中;饶恕与忏悔,体现在女人对于他人的这种关系和解中。忏悔,通往神圣之路的第一步;饶恕,通往与世界、与生命、与他人和解的和平之邸;舍己,通往上帝永恒之地的通行证。
这微弱却坚定的祷告,让瘦弱的她沐浴在圣山第一缕晨光中。此时的女人,躺卧在圣山之下,温顺得像一只小羊羔,如圣徒受洗时的温柔静谧,似停泊港湾的船只般安宁,像柳树安歇溪水旁之安详。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江苏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