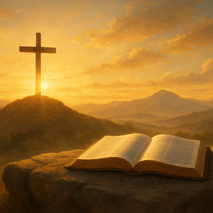在晚清教案的历史透视(三)中,我们谈到了1879年的福建岩兜教案,是一场由文化习俗和经济利益冲突引发,最终在外交干涉下得以解决的地方性民教冲突。它是理解晚清社会内部撕裂与外部压迫之间复杂互动关系的一个重要案例。今天我们接着来谈另一个发生在辽宁省的教案,这个教案也称作1861年“牛庄还堂案”。
当时,牛庄古镇隶属于奉天省海城县(今辽宁省海城市),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古镇。牛庄地处沈阳南部、辽河下游,距离海城市西部20公里处,背靠太子河,东临海城河,北依鞍山市,西接盘锦市,南与营口接壤,处于辽宁中部城市群的重要位置。
牛庄镇历史可追溯至辽金时期,因辽河在此附近入海,商船云集而得名。明代正式建成土城,清天命八年(1623年)重修。1858年,牛庄被列入《天津条约》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61年正式开埠,成为东北地区最早开放的商埠。后来通商口岸迁至营口,牛庄不再作为通商口岸。
关于近代不平等条约中涉及营口(牛庄)的条款,核心在于《天津条约》,并且存在一个著名的 “牛庄开埠”而实际口岸在“营口”的历史事实。
以下是详细的介绍: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这是迫使(牛庄)营口开埠的根本性条约。该条约第十一款规定:“……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欲求汉口、镇江、九江、牛庄四码头通商,……俟粤匪肃清,平靖之后,会谈条款。”意思是说:英国打算从汉口开始,沿江上溯至入海口这一段,挑选不超过三个地方,作为英国船只装卸货物、进行贸易的口岸。他们特别想要汉口、镇江、九江、牛庄这四个码头通商……不过,这些条款要等“粤匪”(指太平天国)被剿灭、局势完全平定之后,再正式开会商定。
一、《中英天津条约》的简单解读与影响
1.首次列入:这是牛庄作为一个县城的小镇首次被写入不平等条约,规定其为新增的通商口岸之一。
2.背景:英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获胜,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特别是尚未被开发的东北市场,要求在中国北方沿海开辟新口岸。牛庄(指当时的辽河古渡口,今海城市牛庄镇)因其在历史上是东北重要的商贸集散地而成为目标。
3.“名不副实”的“码头”和开埠:1861年4月,英国首任驻牛庄领事托马斯·泰勒·密迪乐乘军舰抵达条约指定的开埠地点——牛庄。但他经过勘察发现,由于辽河下游泥沙淤积,大型商船难以航行至牛庄。而更靠近辽河入海口的没沟营(今营口市)河道更深,地理位置更优越,商业潜力更大。
4.单方面更换口岸:密迪乐便依据条约中“港口”和“船舶”等词语的模糊性,单方面强行宣布将通商口岸从牛庄改为下游约45公里处的营口。尽管清政府对此提出异议,但在英方的武力威胁下被迫接受。从此,条约上的“牛庄”在实际开埠时变成了“营口”。这也是为什么在西方历史文献和早期的海关报告中,营口常常被称作“Newchwang”(牛庄的英文旧译)。
二、《中英天津条约》不平等条款带来的列强的主要特权
根据这些条约,列强在营口获得了以下特权:
1.领事裁判权:英国、法国、俄国等国相继在营口设立领事馆,其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管辖。
2.设立租界:列强在营口沿海河一带划定了各自的租界,成为“国中之国”。
3.协定关税:中国海关税率必须与列强“协定”,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于是在当年营口出现了这样一个闹剧也是耻辱:营口海关(俗称“洋关”)长期由英国人担任税务司,管理权落入外国人之手。
4.内河航行权:外国商船和军舰可以自由航行于辽河。
5.传教权:外国传教士可以自由进入东北内地传教,引发了后续一系列的文化冲突和教案。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是营口(牛庄)开埠的法律根源。存在“约开牛庄,实开营口”的历史现象。这既是英国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也是其强权政治的体现。
三、《中英天津条约》的历史影响:
1.积极方面:营口被迫开埠,成为东北第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客观上刺激了东北近代工商业、金融业的兴起,使其迅速成为东北的经济中心和货物吞吐港,营口在当时被称为“小上海”。
2.消极方面:这是中国主权沦丧的标志。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将营口变成了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基地,并以此为据点,加深了对整个东北的政治和经济渗透,是东北半殖民地化的开端。
因此,谈及近代不平等条约中的营口(牛庄),最核心的就是《天津条约》,而其实质开埠于营口,则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
四、牛庄教案始末
1861年春夏之交,传教在牛庄士强行划定归还范围,引发当地士绅与民众不满。6月,数百民众聚集抗议,捣毁临时礼拜场所,驱逐传教士。事件中虽未有外籍人员伤亡,但教堂设施受损。
1861年12月,法国天主教士林貌理依据《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中关于 “归还教堂” 的规定,手持乾隆二十二年(1754年)牛庄 “平民邓林用四十五两银子买下被官府没收的天主堂房产及土地的执照一份,以及白良等人捐赠的公益用地(相关凭证)”,面见牛庄防守尉盛福,请求盛福帮忙查找(上述房产土地)。盛福随即向上级禀报,中法之间关于此事的交涉就此展开。
盛福等人四处寻访当地的乡保(地方基层管理人员)和年长有声望的老人,(他们)称:“在牛庄城以西的新庄子地方,有平民邓玉炜的一处房屋和园地。这处房产是否就是邓林当年买下的、被官府没收的天主堂房产土地,以及(这些房产土地)当初为何被官府没收。由于事情过去太久,没有凭据可以查证。如今在邓玉炜房屋园地以北,隔着一条街的地方,还有一座天主堂,由信教民众白家看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此外,“牛庄西北关新庄子的业主苏克荣等十三户人家,当初买下的天主堂地基有三十二丈五尺,还有十一间草房,(这些数据)与该教士(林貌理)所持印信凭据上记载的数目完全相符。”苏克荣等十三户一听说要查收归还给教会,担心失去住所,民众情绪极为惶恐不安。另外,信教民众白义得指认的、白良捐赠的婴儿坟地公益用地里还有九座不知墓主姓名的坟墓,其余地方都已开垦种地。至于这处土地是否真的是白良捐赠的,传讯乡保和年长老人询问,他们也都表示不知情。
地方官员全面查阅八旗官署和地方民政官署的档案,因事情已过去一百年,档案大多发霉腐烂、残缺不全,最终没有查到邓林买下被官府没收的天主堂房产土地,以及白良等人捐赠公益用地的确实凭据。
上述材料反映出两个问题:第一,中方没有可作为依据的档案案卷;第二,相关房产土地是乡民通过典当、购买获得的,并非私自侵占。因此,传教士要求归还教堂只有单方面证据,从法律层面来讲,“单一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不应将房产土地归还教会。但当时的清政府刚刚经历英法联军之役的惨败,仍心有余悸。所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 “总署”)发文给盛京(今辽宁沈阳)方面,要求归还牛庄的天主堂房产土地,但不包括教会所说的、白家捐赠的婴儿坟地。同时提出可依据此前的皇帝谕旨,“(天主堂)废弃旧址早已改建成民房,势必难以让民众全部搬迁。应按照该国(法国)天主堂原有的土地面积,另外查找官地抵偿给教会。”
然而,此时林貌理已离开牛庄,不知去向,这起案件于是被搁置下来。
1862年5月14日,法国传教士梅依西来到牛庄,要求归还上述房产土地。盛福等人以天主堂旧址距今时间太久、没有凭据查找为由,主张用闲置的荒地抵换,但梅依西坚持索要所谓的 “原址”,若无法满足则要求用旧址隔壁徐、李两姓的房屋抵给教会。地方官员担心一旦开了这个先例,其他地方的传教士会纷纷效仿,造成无穷后患,因此拒绝了这一要求。经过多次交涉,最终商定用官款 “小数钱二千六百八十六千文” 买下教会指认的教堂旧址,限期让十三户住户全部迁出,九座坟墓则保持原样留存。1863 年2月1日,梅依西前来接收(旧址)时,却以尚未偿还原业主邓家(当年购买天主堂房产的)四十五两白银原价为由,拒绝接管。
1864年6月间,因连续下雨,(教堂旧址的)房屋倒塌了八间。总署与法国公使柏尔德密及翻译反复协商,同意为旧址修筑围墙,高度以四五尺为限。
但林貌理回到牛庄后,又额外提出要求,主张必须另外建造一座门楼,才愿意接收(旧址)。牛庄的防守尉和知县为早日了结案件,答应为其建造门楼。总署对此十分不满,表示 “经查,同治四年九月间,接到贵前将军发来的公文,抄录了牛庄防守尉、知县与林教士往来商议地界范围、工程建造方式的文件,并未提及双方签订过合同。如今该公使(柏尔德密)所说的合同,是否就是防守尉、知县发给林教士的照会,无法凭空猜测。只是在这起案件中,防守尉、知县等人不遵守本衙门(总署)的办理原则,擅自与该教士商定工程做法;等到本衙门驳斥(这一做法)后,又不赶紧设法处理。这是既在事前擅自做主,又在事后拖延推诿,实在不合规矩。但该教士持有防守尉、知县等人加盖官印的文书作为凭据,本衙门怎能仅靠言辞争辩(推翻)?现令防守尉、知县遵照此前的商议结果(办理),若传教士不遵守,则筹备款项(另行)处理。” 最终,(总署)与法国公使兰盟商议,按照最初的议定方案动工,为教堂修筑围墙,高度以五尺为标准,围墙总长度凑足九十丈,门楼则从简修缮,总共耗费白银三千四百余两。法国驻华公使哥士耆(Michel Kleczkowski)向总理衙门施压,清廷责令盛京将军玉明查办。最终,地方官赔偿教堂损失并划拨新地建房; 涉事民众遭惩处,官员被申饬;传教士获准在牛庄建立新堂(后成为辽南天主教中心)。
1868年8月,传教士接收(教堂及相关设施),历时七年的牛庄还堂案终于了结。
五、牛庄教案的后果和影响
关于1861年辽宁海城牛庄的“还堂教案”,这一事件是清末基督教在华传播过程中与地方社会产生摩擦的典型案例。
1.典型的“条约传教”冲突
此案凸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活动依靠不平等条约强制推行,地方官在“保教”条款与民情之间进退两难。
2.东北民众反教先声
牛庄教案是近代东北最早的反教事件之一,与同期南方教案形成呼应,反映底层社会对西方势力深入的内生排斥。这里需提及一位人物——齐凤仙:牛庄人,1900年6月,他与西土台人张某分别号称 “岳元帅”和“杨元帅”,组织 “神拳营”、“红灯照”,领导牛庄义和团运动。当时牛庄义和团发展到三四百人,海城全县发展到千余人。农历六月初十,当盛京教堂被义和团烧毁的消息传来时,牛庄义和团 200 余人在齐凤仙的带领下,活捉并砍死了法国传教士大司泽,还放火焚毁了教堂。
3.殖民秩序的建立
清廷的妥协强化了法国在东北的宗教保护权,此后直至义和团运动前,辽宁地区发生类似教案二十余起,均以外交压服告终。
这一事件不仅是宗教冲突,更是晚清中国被迫卷入全球化进程中,地方社会应对殖民扩张的一个缩影。
牛庄教案给我们今天的启示是:不能否认传教事伴随着当时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的;由于当时清朝政府的懦弱和妥协,造成了传教士在中国领土的飞扬跋扈;但是随着西方列强带来的先进科学基础理念和传教士的慈善公益事业等也给东北带来了诸如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改善和提升;牛庄教案告诉我们:宗教必须中国化,宗教必须在政府的领导下。
参考数目:
1.原始档案见于《清末教案》《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2.现代研究可参考《谣言与近代教案》苏萍著作、《早期东北基督教研究》张建华等著作
3.《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606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自张力等著作
4.《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页。[澳]骆惠敏编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